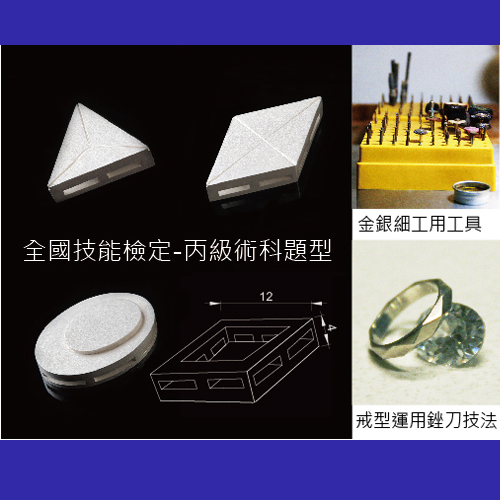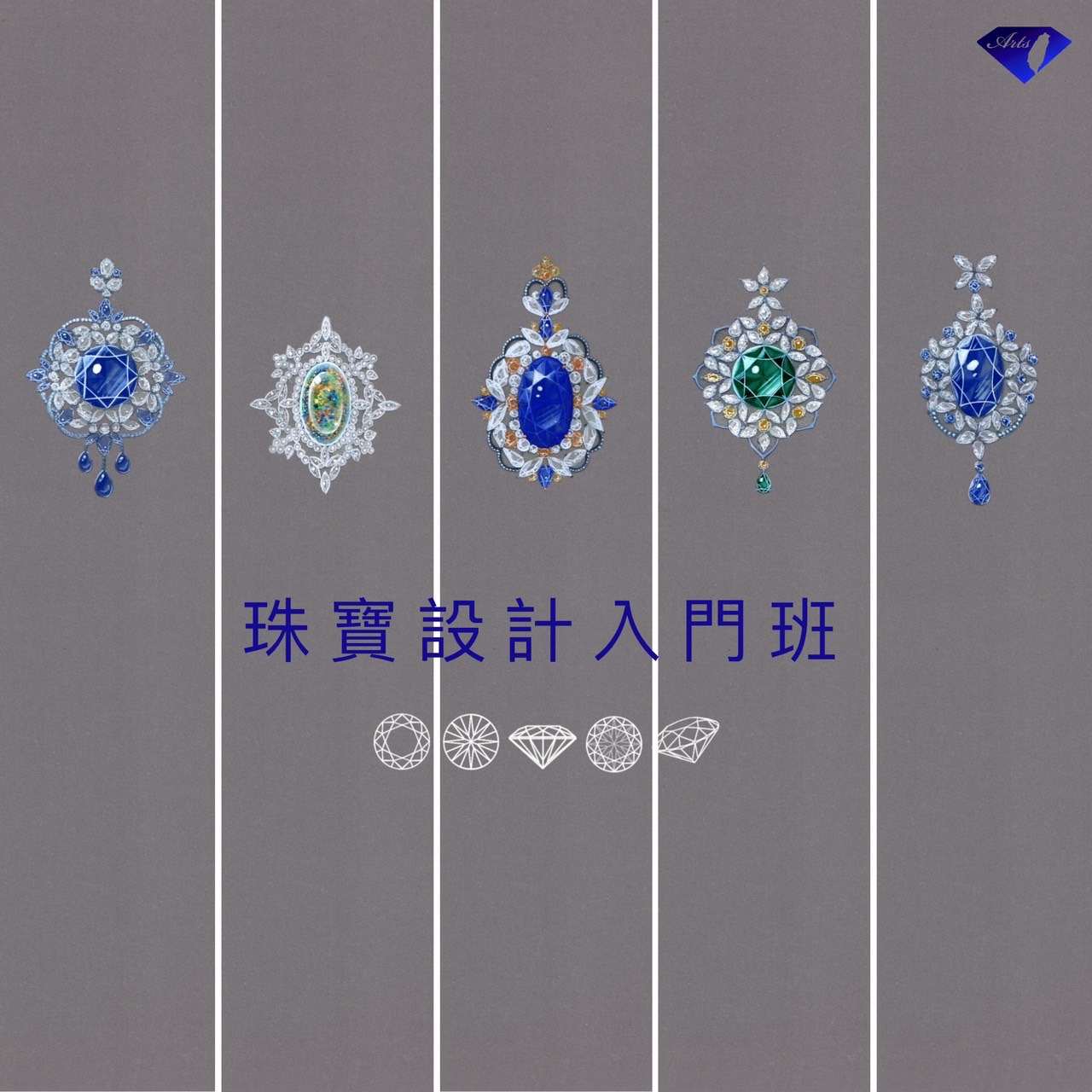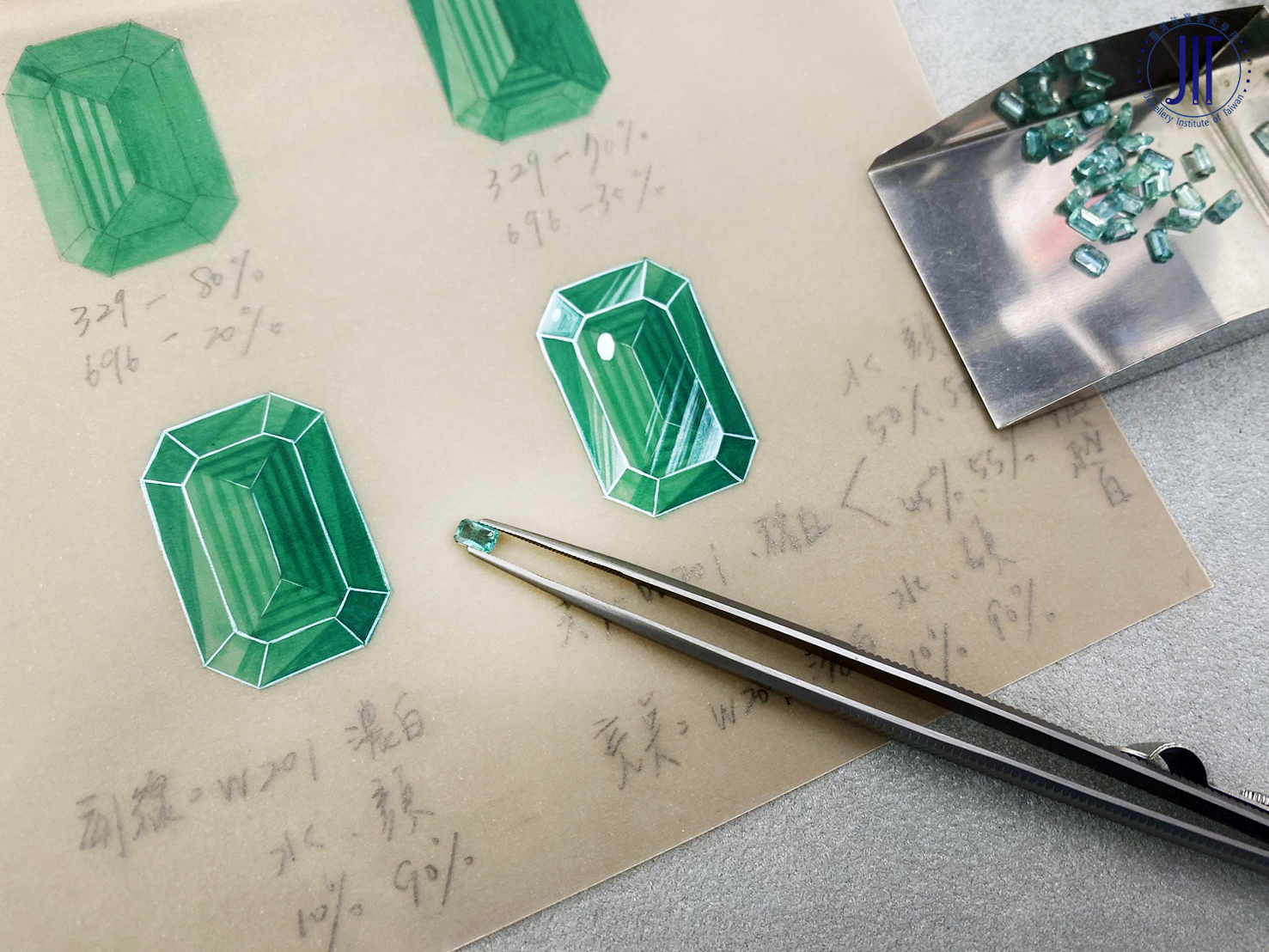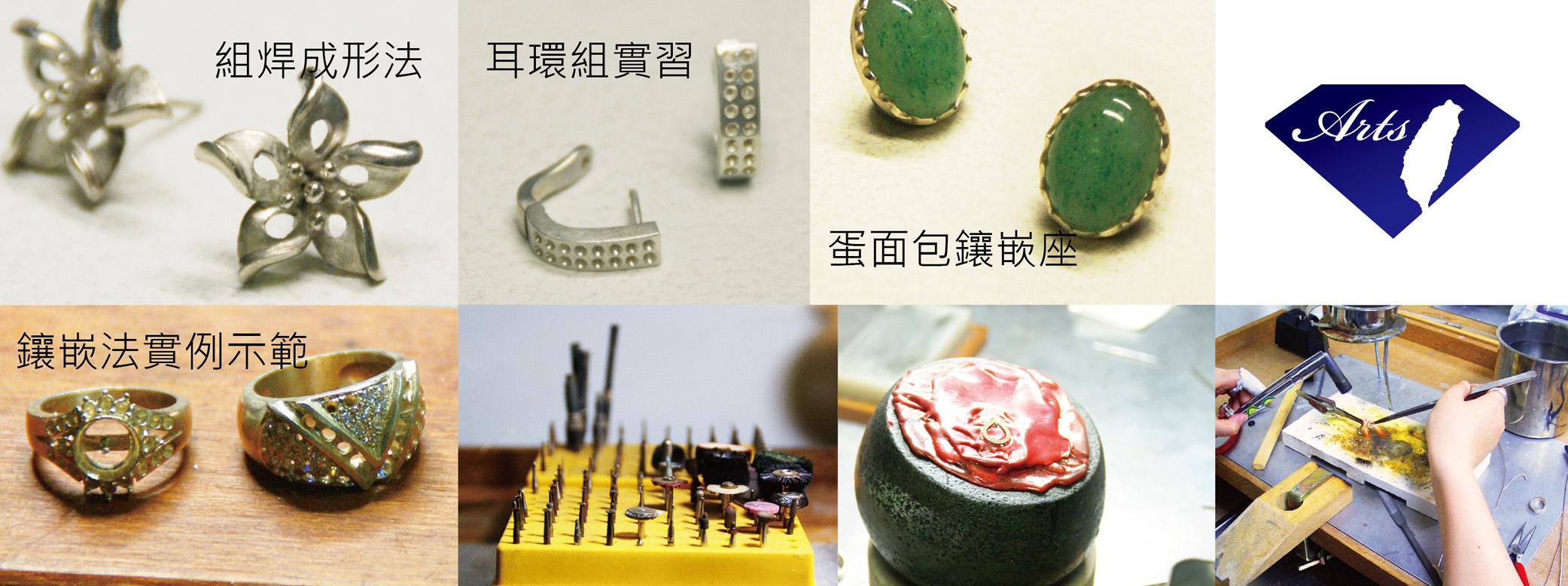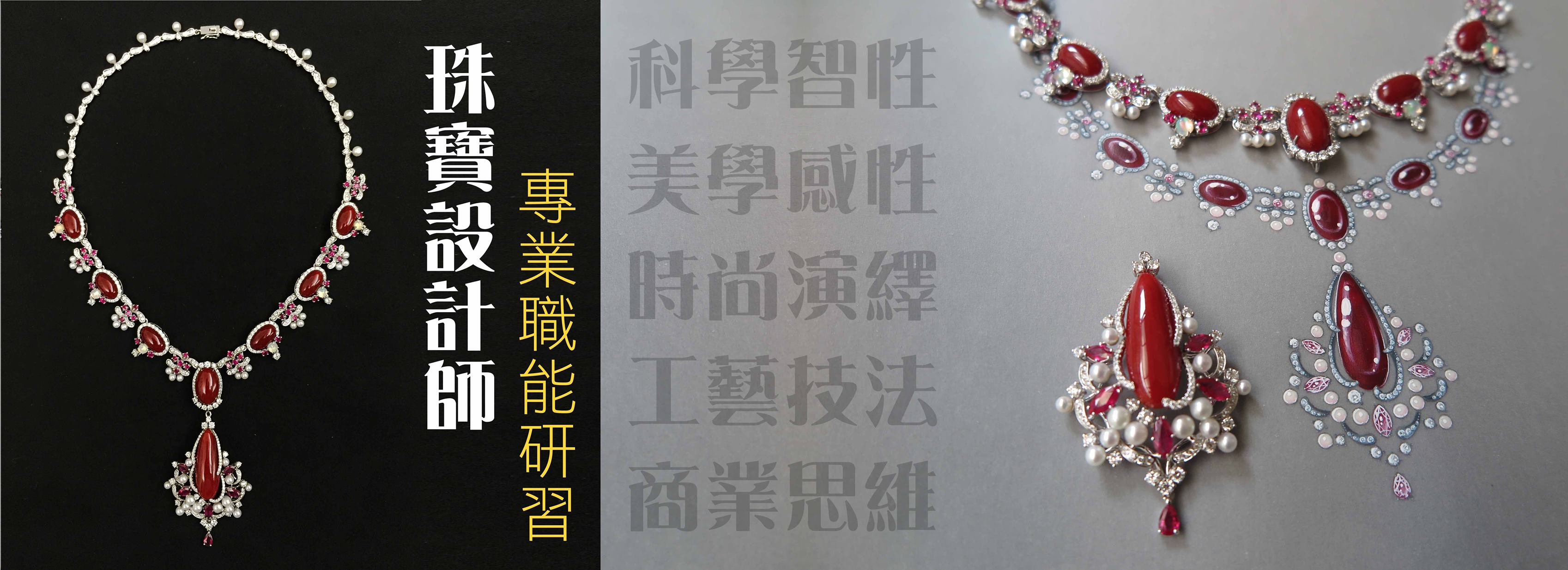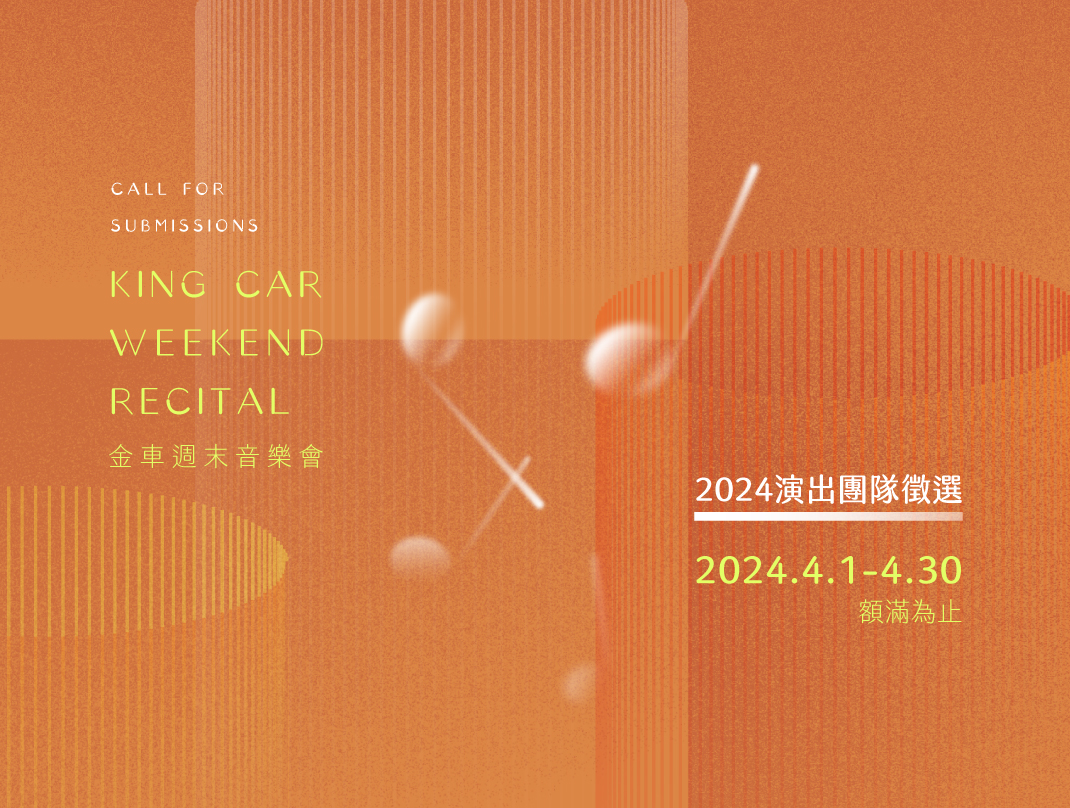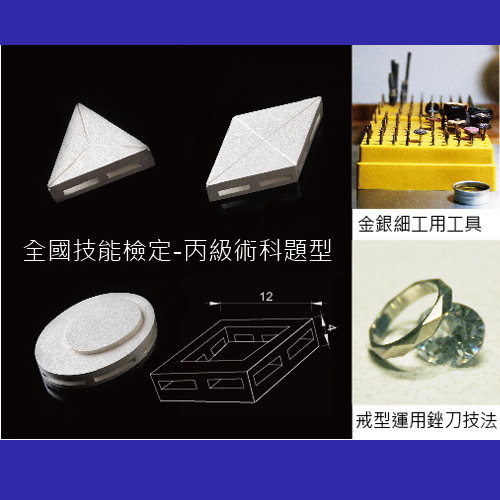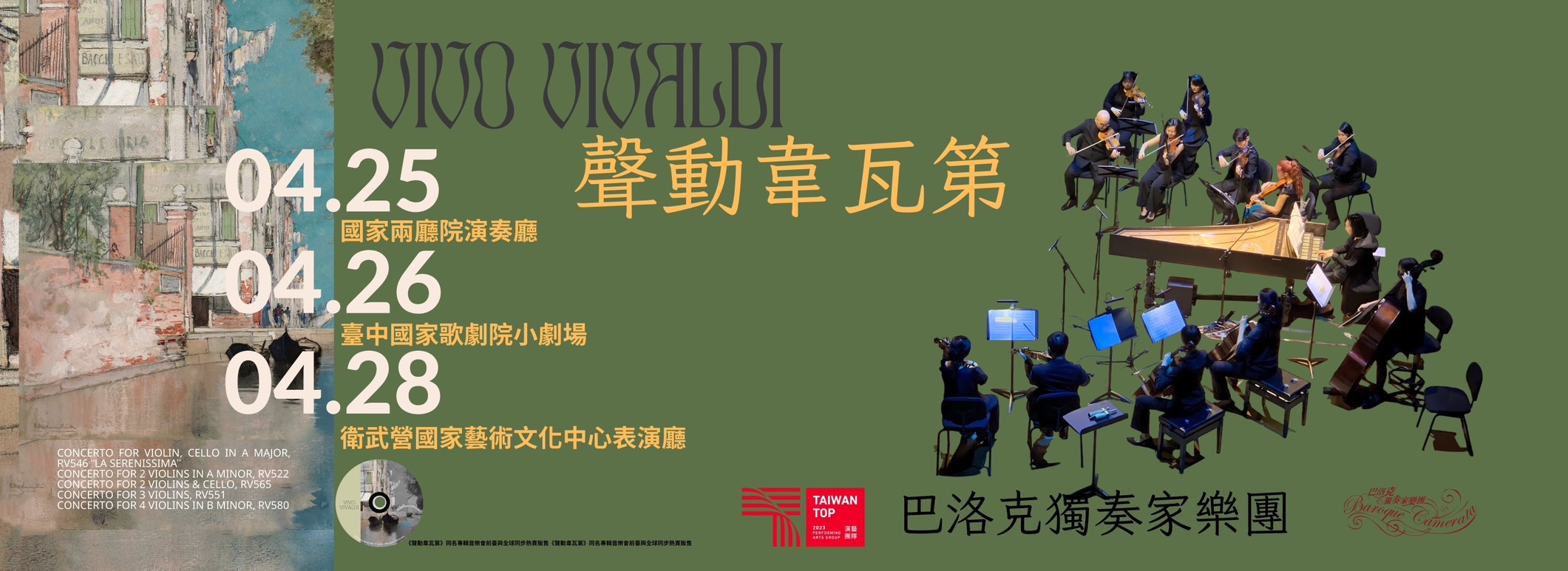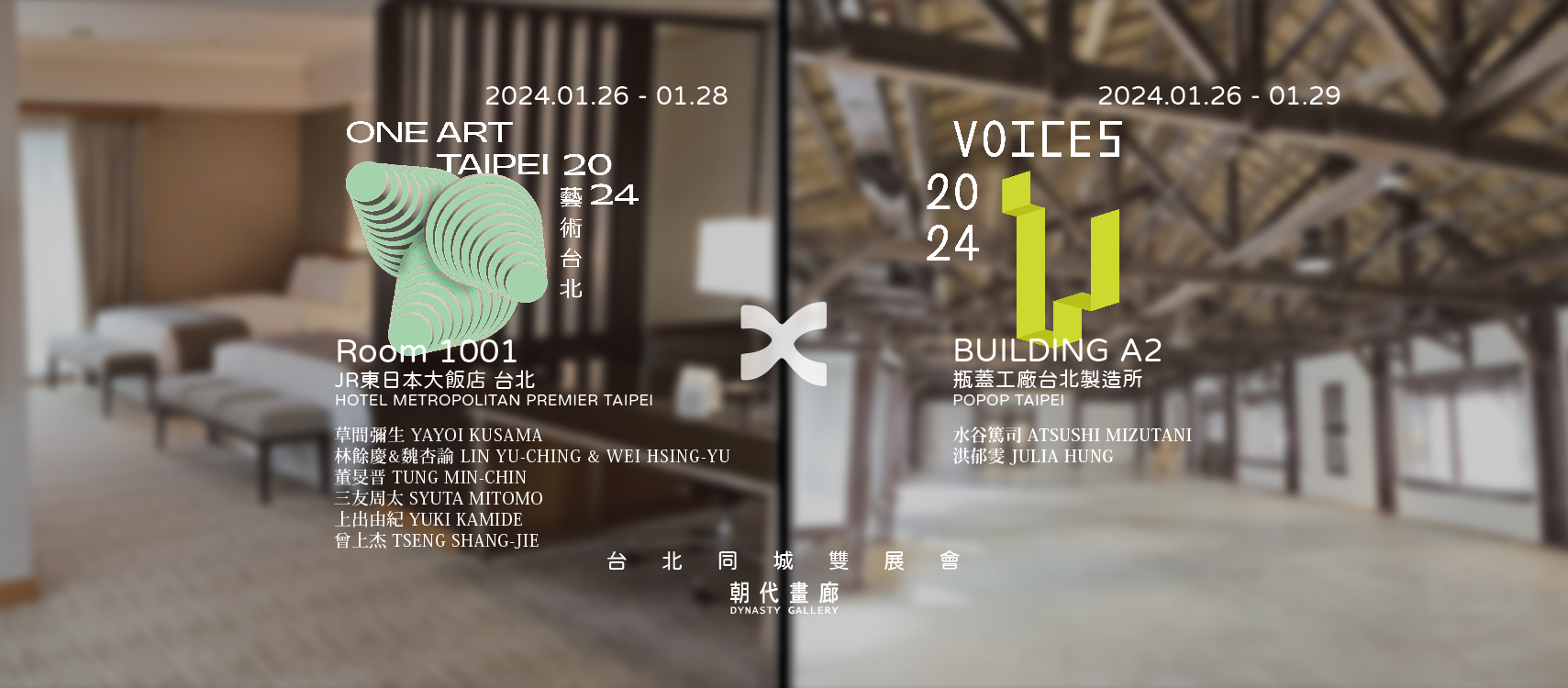當一位藝術創作者以藝術家的身份來為生命意義定位,他將讓自己成為和魔鬼處於交易狀態的浮士德。浮士德與魔鬼打賭,他立誓,當自己高嚷著:「你真美呀,停留一下!」時,停頓將使他委身於魔鬼。面對自己的藝術之路,洪明爵道出:「我覺得藝術的坎坷和辛苦不在於你的才華,而是長久堅持的理念和想法。」必須堅持的太多,可以妥協的太少,藝術家的藝術之路只有一條鋼索那麼寬。
什麼是神話?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認為神話的定義是體驗生命,藉由神話,我們可以瞭解人類生命的原型。洪明爵的藝術之路是在尋找藝術的原型,伴隨著對生命的咀嚼過程。畫家說:「……面對的就是,對於我活在世界上的定位質疑。」在他尋找自己的神話歷程中,除了無法遏止的回溯,更是充滿激烈的割裂與叛離。
城市浸染鄉村
洪明爵於1968年出生於屏東縣琉球鄉,父親身兼木匠、捕魚二職,面對三男三女的龐大家計壓力,在1974年舉家搬遷至東港定居。
畫家在論文對自己成長背景作了清楚的敘述:「此時的東港,正值開發的處女之地,到處充滿商機,父親的到來自然也趕上了這一波風潮,全家的生活問題也因此免於愁雲慘霧之中。在東港的九年裡,經歷了國小、國中的階段,可以說是懂事以來的第一個故鄉。回憶起這些日子,較深刻的印象應該是『教會的參與』、『學校的活動』與『習畫』三件事;之所以到教會,就是那單純又嚴肅的爸爸所希望你去的地方,你是別無選擇的。而畫圖的影響可就大了,它感染了我全身的細胞並驅使我一生走往藝術的道路而去,直到今天。」(註一)
在1983年,洪明爵在國中美術老師葛小蓉的鼓勵下,隻身前往台北求學。都市的車水馬龍、五光十色、現實的人情世故,與家鄉的船笛、純樸、濃郁家族親情間,呈現矛盾對比與衝擊的狀態。就讀大學時,PUB與舞廳成為他人生經驗中與年少輕狂無法二分的歷練。
正如坎伯明白揭示的:「我不相信有平凡的朽物這回事。任何人在生活的經驗中,都有他自己精神上狂喜的可能。他要做的只是去認識它、修練它,並與它同在。當人們說到平凡的朽物,我總覺得不舒服,因為我從未見過一個平凡的人、女人或小孩。」(註二)所以勇於面對生命經驗中的種種,就是讓自己真正活著的方式,更可成就神話中的英雄冒險。為尋找神話,生活中的點滴感觸、甚至對故鄉依戀似的回顧,均成為洪明爵的創作動因。
對人性的描繪
洪明爵早先是以油畫為主要創造媒材,1991年的《城市英雄系列》畫作中,注重的不是對物象的模仿,在畫幅上我們看到形體框架中極富表現性的筆觸,及小部分運用色面的平塗手法。畫幅上人物有的三五成群、有的獨坐一旁,人物臉孔在小色面筆觸下並不明晰,但隱約可見大家的眼光不是斜眼朝外、就是托腮呆望、陷入無語的垂視,似乎因為茫然,使撇向觀者的眼光也毫無神韻。都會夜生活的虛無與閒晃味道,在不規則的筆觸下,更見迷惘的心緒。
現代藝評之父查爾斯‧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認為,藝術的本質在於對「現代性」的掌握,透過藝術家敏銳的觀察力,不僅每個時代會有它自己的步調,而且「現代性」也因不同的國家、民族,而有多樣的揣摩與表現。洪明爵在1992年獲得47屆全省美展的優選的油畫作品《徘徊台北的夜》,整幅畫的畫面籠罩在近乎象徵式的暗色調中,一塊塊顏料,畫家讓都市中暗夜徘徊的未歸人迷惘畢現。
童年印象的抓取
不知是誰說過,人們總憑著影像來回憶某些事件。因藉由影像可找出過去事件的情節,所以似曾相似的影像總可輕易抒解人們對過去的依戀。洪明爵的畫作中,發現其對童年熟悉故鄉的重建。在1990年得獎的油畫作品《東港》及《漁市場》,港邊巨大的船與魚市中忙碌的身影,在印象派筆觸的運用下,一個個剪影式的忙碌身形躍於畫布上,似乎看到小時候的畫家也蹲踞在畫面一旁。
洪明爵的畫作,總有種水氣氤氳的味道,好像並不受限於媒材。油畫作品中,由於同色系的油畫色料疊置,主體也沒有明顯的輪廓線,所以,畫面總有種濛濛濕氣的感覺。到了1995年後的油畫作品更是色料直接暈染到其它色料上,用色不因主體的固有色而有所侷限,反有以色喻情的狀況,象徵意味極濃。如在油畫作品《唯我獨尊》、《東港修船廠》等中,以表現派的的創造精神,強烈色彩的對比,甚至色與色間互相掩蓋的狀態,均為直指內在精神的捕捉。顯著裝飾色面的蔓延效果,使人似乎看到流動的顏料,在1997年抽象表現派似的油畫作品《藍色組曲》中,我們漸漸感到畫家自我對水性的降服。
對水性的追求
在1995年後,畫家開始以水彩作為主要的創作媒材,他自道因為較喜歡水的感覺。水與水彩甚至後來的水性顏料,成為洪明爵對自我神話追尋中的顯著象徵。港口、捕魚等意象,成為諸多水彩畫作的主要題材,早晨、黃昏、陰天、晴天、濃霧未散的港邊景象,似乎是畫家無法遏止的反芻行為的成果。
水彩顏料的掌握,需要的是瞬息間幾乎流於直覺的拿捏,對色相、水份、濃淡的掌握稍一不準確,筆觸一猶豫不決,造成的結果可能就不堪入目。畫家喜歡水水的感覺,是否是因港邊子弟的海洋性格所導致,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但可想見,其心靈是不斷跳動的不定體,一反應在技法上,就是隨時在變的多重表現。
相較於油畫,洪明爵水彩畫作中的人物,五官神韻捕捉的更為明晰,畫家明快的筆觸下,主題人物的個性毫無遮掩的被揭露,呈現的深度超越快照般的表象。這樣深層的揭露,題材不僅著眼於對社會現象的認知,更延伸到畫家個人的種種感觸。
在1995年,得到第50屆全省美展第一名的水彩作品《曾經》,及同年得獎的水彩畫作《等待》、《少女情懷》,其中《少女情懷》是作者少見的以細緻感為主的水彩作品,構圖有濃厚的法國學院派古典油畫章法的韻味,油燈籠罩下的暖色調更顯典雅。相較之下,《曾經》、《等待》的畫面色調就較為活潑,場景與構圖的安排,都是對於形式美感高標準要求的例證。在畫家功力的掌握下,水與彩的互動既調和又能呈現出東方水墨的韻味,更具備了西方水彩創作的艱深素描基底。
藝術的體現無法超越時代的氛圍,同樣的神話的追求也是如此,正如坎伯明示的:「象徵領域的基礎是特定社群的人們,在某一特定時空下所有的經驗。神話密切的受限於文化、時間、空間,所以除非象徵符號或隱喻能透過藝術的不斷創造而加以保存,生命便會從它們之中溜逝。」(註三)在洪明爵的水彩畫作中,波特萊爾所激賞的現代性從未缺席,過去似乎因而停留。
在水彩作品《放學後》中,一位小孩看似自得其樂的玩著自己的遊戲,畫中黃色的紙飛機十分顯眼,因著小孩的注視目光、加著紙飛機似乎將往下方飛去的暗示,整幅畫更見動感。在作業簿上的鑰匙,明示著他是一個鑰匙兒童,父母雙薪工作漸成趨勢的台灣社會,這樣的教養問題在畫家的揣摩中,及深刻揭露下,已是富有社會意涵的永恆見證。
畫家以明澄的眼睛,觀看著這時空中獨一無二的種種情愫、疑慮、期許,他不輕易容許這些轉瞬即逝的感動消失,以畫筆成就這些感觸的永恆,以畫筆紀錄對家鄉的緬懷情懷。1996年得高雄市美展第二名的水彩作品《不安》,畫中暗沈色澤的牆壁,床鋪上的人頭骨,角落未點著的油燈等,加上主角的凝滯神情,似乎連小提琴的音調都是走調的。同年得獎的水彩作品《昔日》,在破碎的玻璃外,港邊輪船的鮮麗色澤顯得有些刺眼;為什麼現在的世界顯得黯淡,為什麼過去的回憶總是如此明亮?
在1997年完成的水彩作品《期許》中,母親雙手輕搭下的小小肩膀,是一個手執小提琴的小女孩,她直視著觀者,對於家長對她的期許似乎明白也似乎迷惘,在水彩暈染的效果下,更彰顯殷切的期盼,熱切得似乎要燃燒起來。
相對於《靜夜》的明亮色調,《期待》與《困》在水彩互相渲染下交雜出的暗色背景則沈重許多。《期待》中,孕育生命的小女生,膝蓋以下慢慢淹沒在暗色系的水彩中,低垂的青稚臉龐在沒有光暈的畫幅中,顯得無助且孤立。《困》中,薄塗的藍色水彩看似裊裊炊煙般輕飄飄的,連鳥兒都飛走了,是什麼可以阻止人們離開呢?是否因為沒有勇氣,才對受困甘之如飴、視若無睹?
叛離畫筆的前奏
在1994年,台北市美展特設國內首創的「綜合媒材」比賽類別,直接以獎勵為綜合媒材表現的正當性作定位。所謂綜合媒材或複合媒材的表現,除了平面繪畫的多種媒材混合表現外,更有利用實物拼貼來創造畫面凹凸的肌理等。洪明爵自1996年起,如畫作《少女的煩惱》、《想飛》、《KTV》等作品中,已開始運用複合媒材為表現手法,在透明與不透明媒材對峙、黏貼物的使用中,結構及肌理的堆砌在複合媒材的使用下有了更寬廣的可能。畫家自道,「……水彩並非不好,而是如何更自在的揮灑,不受限於它的透明性及宣染性,使肌理及結構更具變化性。」
1997年創作的複合媒材作品《少女》,獲得1998年第53屆全省美展的第一名,而油畫作品 《為現在而進行》更摘下1998年第15屆全國美展第一名。在1998年,洪明爵集榮耀於一身,然這樣的肯定是否即是讓他想留駐的美好呢?
終結具像的儀式
油畫作品《為現在而進行》的創作前因,洪明爵道出,「覺得該畫一張寫實的作品,為對自己寫實的努力作一階段記錄」。在蒐集構圖素材之前置作業耗時極久,為求構圖的一絲不苟,嘗試用V8拍攝作畫題材,在電視上放映所擺放的靜物,細查構圖上是否做到全然完備,定稿後再用電腦列印出,再視效果作最後的構圖調整。進行儀式前的準備完成後,畫家開始對著實物進行具像描繪作畫的儀式。
為兩個多月的作畫過程,似可命名為寫實的紀念儀式。畫家曾口述那段期間的感觸:「在作畫的過程,我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我自己告訴自己,一定要有耐心的去完成它…..或許是個性的因子不斷的自訴:自然的模寫是唯一創作的方法嗎?那種心靈、識曾相似、模糊的影像不斷地向我招手,似乎在訴說著:你可以繼續走下去,只是別那麼在意形象即可。」
原始社會的成人禮,有打落牙齒、割包皮等各式各樣的典禮,他們認為,在儀式執行完畢後,那個個體也將有蛻變般的變身效果。就像原始社會中的藉由儀式來蛻去舊有的軀殼一樣,洪明爵在這兩個多月的寫實儀式後,終結具象寫實。
離開的心境
為什麼離開具像?畫家說:「最明顯的轉折點應該是比賽。比賽給人帶來的是信心,也可能是挫敗。這個信心也使我多了些創作的動力,更不願因此沈溺於自滿,一生就守著這種得來不易的成就直到老、死,我看過太多這種例子。」一得獎,畫家就怕自己迷失在聖化的光環下,走在藝術之路上,若停頓,將立即委身於魔鬼,洪明爵不想成為第二個藝術家浮士德。
為了求進,一定得離開具象嗎?畫家又說:「….從具象的描繪裡面我一直有種感覺,那不是我。因此,我一直處於矛盾、不安的狀態。不安不是沒有安全感,而是對畫面的不安,不願意一直去研究畫面技巧,而是去研究怎麼找到自我。」是的,因為想要創造自我,就非得尋找出屬於自己的神話,但自己在哪裡?
怎麼尋找自己?坎伯說著,「我們一生會有許多經驗,有時或有一些讓我們對此有些了解,並對何處是你內心直覺的喜悅,提供一些線索。抓住它,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它會是什麼。你必須學習認識自己的深度。」(註四)順著自己內心的喜悅,那就是自己。
畫家回到自己的童年,他說:「我小時候很喜歡撿東西……。我爸爸是一個木匠,從小就常常在他的工作坊裡面玩小木塊的堆積,並撿了很多放在我的抽屜裡面,我抽屜盡是一些很噁心的東西,鐵絲、髒抹布、髒木塊、鐵釘、石塊等等。我曾經還作過老鷹,用鐵絲綑綁成一隻老鷹。我在想,那個應該就是原來的我。」
柏拉圖輕視畫家,是因他認為,畫家只能觸及到事物真理極小的部分,形象的模仿仍離真理非常遠。然洪明爵的離開具像,不含貶抑的成分,為的是原來的他,他為了追尋到的自己,反叛了再現的國度。
一直的堅持
洪明爵在大學時期,是以油畫創作為主。1995年起,開始嘗試水彩創作。1996年便已蒙發複合媒材的創作形式。自1990年從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後,在1999年考取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創作組榜首,研究所階段的他,尋到畫筆之外的另一種創作模式。
他正在尋找神話的定義,洪明爵說:「我不敢肯定自己將來一定會走平面創作這條路,還是會走到裝置藝術、觀念藝術、甚至到最後是展示某些現象的一些東西,我都不去設限。因為尋找自我潛在的特質是從小到大一直在做的,我想很多人都會有這經驗的,但這樣個性的人也有很多缺點,比如說,在一個風格還沒有成形、穩定之前,很容易被自己否定掉。……但是,我常覺得我就是那個樣子,我還沒有找到,我就繼續找。」
在洪明爵的作品中,對社會現象的詮釋及揣摩一直佔著極大的部分,這個特質,並未隨著他在尋找自己的過程中消失。我們可以這樣說,他的充沛內在活力與這時代環境交相摩擦出的火花,是支持著他,繼續行走於漆黑的藝術路上的微弱光源。
在作品形式上,我們發覺在畫家作畫時,背後總有著極為嚴格的形式美感邏輯在監控著他的一舉一動。然在媒材、肌理的運用上,我們看到比較多屬於畫家自己的因子,我們暫時可以這樣說,洪明爵在媒材、肌理的處理、取捨上,的確暴露出較多屬於私密性的個人特質。
熱的抽象
在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創作組就學期間,洪明爵的創作漸往熱的抽象路徑邁出,在2000年的的複合媒材作品中,我們看到這樣巨大的轉變。他將對個人、社會、事件等的各種感觸,通通化為抽象的藝術形式。
由具像急轉至抽象,我們就著畫家的作品看來,早期創作中關於教堂,及為行人行進馬路而規劃的斑馬線,是隱約可見的具像輪廓。如在《城市護衛》、《迷濛中的教堂》中的教堂輪廓,及《記憶圖像》、《珍貴的白》等作品中的斑馬線,教堂象徵的宗教秩序、斑馬線象徵的形人行走規則,這樣的象徵在人類社會個體眼中,有十分明顯的社會意涵,縱使它們只是幾何線的構成。除卻幾何形式上的美感之外,仍有豐富的象徵意涵在其中。
洪明爵的抽象作品中,有著濃厚的表現主義精神,及部分超現實派畫家對心靈自動性的嚮往。如《擴散中的紅》、《山河變》、《心靈圖像》等作品中,蔓延的色料似乎緊跟著畫家的情感起伏而擴散。以熱的抽象稱呼之,是因為相對於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的知性的、直線的嚴肅冷抽象,洪明爵的抽象創作有著更為感性、直觀的浪漫及神秘性的氛圍。
在2000年後的抽象複合媒材創作作品上,我們發現畫作上形式的有機特性。不知怎地,那些表現性的形式語彙中,有明顯的水的意象,有水般流動的曲線,有水泡般一圈又一圈的痕跡,更有一種水不停滲透的蔓延味道,有的形式竟讓人聯想到水漬。是否在回歸自我神話的路上,畫家又回到童年的港邊,直接躍入小時候的海裡。
在尋找自己的藝術之路上,洪明爵說著:「…..藝術工作至少對我來講比較快樂一點,或許因為我可以為所欲為的創作。人們常問我,到底有多少人懂得欣賞你的作品,其實那已經沒那麼重要了,有時候,如果你把創作當成你的一生,它就像是一部日記,它記錄你一生所吸收到的的知識,紀錄你一生的種種想法。……事實上就是那樣的一個感覺,它記錄我的成長過程,記錄我對藝術的看法,記錄我對社會的看法,記錄我對於人的看法的一個過程。」
生存在全球世界主義下的藝術家
現在,全球世界主義在媒體、科技的推波助瀾下,各種思潮、藝術理念、創作模式等的多元狀態,不是區區的地域性就可以完全防堵的。破裂、無法預測、失去確定性的多元,加上世界村的現象,我們可以說,這個世界的外人將消失。畫家處在這樣的時代,各種藝術理念化成資訊般迅速傳播,什麼是藝術?藝術的樣貌如何可見呢?全世界的藝術家如瞎子摸象般的預言著自己意識到的藝術樣態。
洪明爵身處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在這連所謂傳統幾乎都不再有絕對主導性的時代,他要怎樣尋找到屬於自己的神話?畫家說著:「不管怎麼說,我希望畫面裡能夠有屬於自己的造型方式,但又不希望走到純粹的抽象。因為純粹抽象裡,是抽離內容的部分,重點只在於傳達視覺美感,或是說純粹的畫面造型結構安排。並非我所研究的對象。我只希望能夠在抽象造型觀念中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人生哲理來開拓,雖困難、道路本身也很狹隘,但這種狹隘也是讓我較為深入的一種做法。」
去傳統時代下的種種反思,或許所謂的主義已無法主導藝術創作模式,在現今的藝術世界中,種種支配風格、樣態的規則,不再有絕對的存在空間。唯一能抉擇的,是藝術家該誠實面對更適合自己的創作形式,並耕耘它。
回歸自己
洪明爵在2001年後的創作模式,改以木製夾板作為畫布,作出大畫幅的複合媒材創作。這時作品的另藝術(Un Art Autre)風格,畫家說在創作中受到西班牙畫家安東尼‧達比埃斯(Antonio Tápies)的諸多啟發。
另藝術畫家,因為善於利用各種材料表現,故將物質的觀念引入畫面中,這與一般繪畫觀念是不同的。洪明爵運用各種媒材,來將自己的種種感觸寄託在畫面結構、肌理、形式中。在《僅存的存在》作品中,畫家運用貼裱(collage)的技巧將香菸盒包裝貼在畫面上,層層的白色企圖掩蓋有著紅色十字架的教堂。畫家說:「……畫面下方白白的地方是一個教堂,教堂整個都被白色所掩蓋掉,剩下一個殘缺不全的十字架。如果連這十字架的支撐都沒了,那麼,人們對於未來未知的寄託將何去何從?」
在《未知的迷惘》中,巫祈占卜用留下的甲骨文,及十字架、佛手等符號的並置,各種符號與象徵在此畫面上,未知就可以預視了嗎?在《大地的守護神》中,在富有生命力的土黃色面中,有著各式各樣階梯式的肌理,其中一個突出土黃色塊的階梯上,站著一個雙手大張的人形,畫家說:「印地安之神已經站在上面了。」
畫家曾說,「我小時候受到宗教的影響蠻大的,到今天我還在尋找那神秘的未知領域…」,教會是畫家童年記憶中印象最深的場所,十字架雖只是二條直線相交的十字形,但在畫家回溯自我的時刻,卻是最難釋懷的符號。
在《生命的延續》作品中,一個個相交的不規則圓形物,像極了在黑暗海底漂浮的一個個泡沫。在《紅與灰》中,我們看到另一種美學的存在,強烈的韻律、富有創造力的肌理,這是畫家將內在思索以視覺藝術的模式再現出的成果,就如同畫家自述的,「……我很難想像在無意識狀態下要如何作畫?無意識之下是很難下筆的,所以我傾向藝術創作是一種有意識的行為,而且藝術創作可以喚醒那無意識的部分。」
洪明爵就像立誓般的道出,「我永遠不放棄視覺上的經驗、美感。」這樣的堅持,就如同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認定的,作為藝術的僕人,畫家必須的義務,就是提供一般藝術所特有的東西。
無法停止的薛西佛斯
在尋找自己的神話中,洪明爵經歷了不斷否定又再重建的過程,這多像薛西佛斯,必須重複經歷推動石頭上山的喜悅,及目睹石頭從山頭滾落的痛。
畫家堅持著尋找自己的神話,他的創作,不停的從畫家身上吸取養分,有著畫家的童年、喜好、感觸、故鄉、疑惑、愛………。在畫家充沛內在活力滋養下,這些作品在誕生之際,就擁有自己的生命主體。
只有鋼索般寬的藝術之路,可以妥協的太少,必須堅持的好多、好多,然他仍須不斷的尋找自己的神話。難道他不怕神話是謊言嗎?坎伯解釋說,「不,神話不是謊言,神話是詩,它是隱喻的。有一種說法很好,神話是準終極真實(the penultimate truth),因為終極真實不能化為語言。它是超越語言,超越意象,超越佛教再生輪迴的限定邊緣。神話把心投向那輪迴之外的世界,投向那可以知道,但不能說出的世界。所以這是準終極真實。」(註五)
終極真實的神話何其可貴,相信畫家不會停止尋找自己的神話。
【註解】
(註一) 洪明爵著,《【認知與現象】創作研究》碩士論文,2001年,pp.74-75。
(註二)Joseph Campbell&Bill Moyers著,《神話》,朱侃如譯,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p.280。
(註三))Joseph Campbell&Bill Moyers著,《神話》,朱侃如譯,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p.104。
(註四)Joseph Campbell&Bill Moyers著,《神話》,朱侃如譯,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p.205。
(註五))Joseph Campbell&Bill Moyers著,《神話》,朱侃如譯,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p.281。
【參考書目】
何政廣著,《歐美現代美術》,藝術家出版社,1997年。
歌德著,《浮士德》,海明譯,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78年。
Baudelair,Charles,”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Phaidon Publishers Inc.,1964,pp.1-15.
Joseph Campbell&Bill Moyers著,《神話》(The Power of Myth),朱侃如譯,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